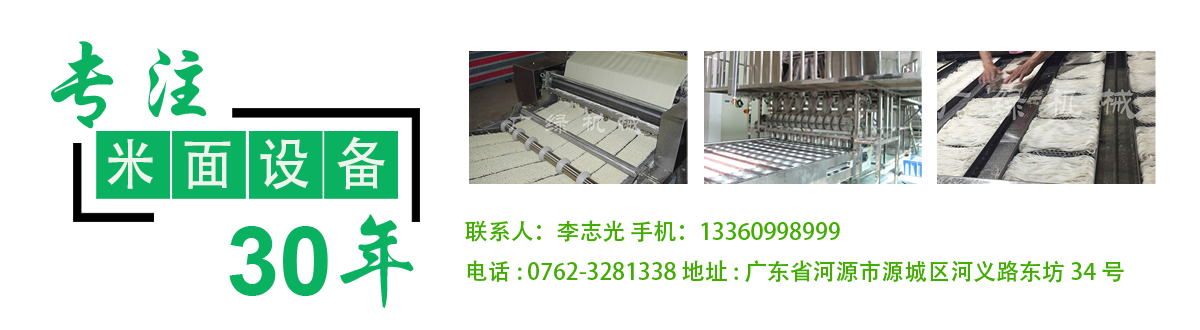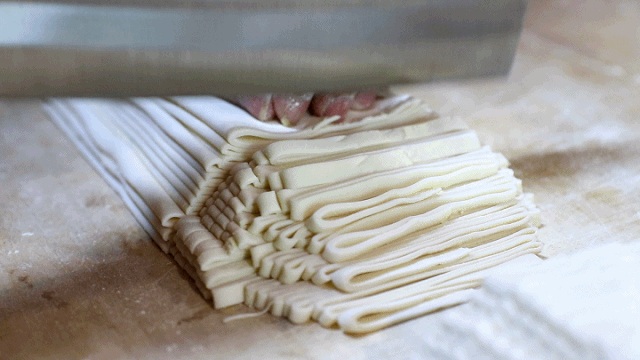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句流傳(chuán)很廣的話,叫“吃(chī)米不如吃麵,走親戚不如(rú)住店。”第一次聽(tīng)到這句話時,其時還小,不大(dà)理解為什麽吃米不(bú)如吃麵,但對後一句卻(què)是有感悟的,大約說的是人(rén)情薄如紙。
關於人情,正是撓到人世(shì)的癢處。痛可(kě)忍(rěn),癢不可忍。雖不可忍,也不(bú)便多言。
還是說吃吧。吃米(mǐ)和吃麵,哪個如哪個,哪(nǎ)個不如哪個(gè),也沒有定論。我看,之所以有這句話,是用了詩經的表現手法——“賦(fù)比興”中的“興”,以某事物為發端,引起所詠之事。又很押韻。但這句話的前半句,可以作為話題談。
國中作物分布大致(zhì)是南稻北麥。若以河流劃分,則長江(jiāng)流域(yù)吃米,黃(huáng)河流域吃麵。我出(chū)生在黃河之陰,小(xiǎo)時候(hòu)就(jiù)心理距離而言(yán),離長(zhǎng)江十萬八千裏,自然以吃(chī)麵為主打。米也吃,但吃的是黃米,一種軟(ruǎn)的,做(zuò)糕用;一種硬的,也叫糜米,做米飯(fàn)用;一種叫穀米(mǐ),也就是學(xué)名叫(jiào)小米的那(nà)種,一般用做熬稀粥。吃米僅此。吃(chī)大米是後來的事。吃麵(miàn)居(jū)多。

白麵是小麥脫粒磨碎的產物。饅頭、麵條(tiáo)、烙餅(bǐng),是白麵做成飯食的三種最重要的形態。饅頭輔以燴(huì)酸菜。麵條,豬肉臊子。油烙餅,炒山藥芥芥,或炒雞蛋。有時也吃蒸(zhēng)餅、鍋貼、花卷,大同小異,麻(má)花、油炸炸、油條、油餅等,就是那團麵,隨便(biàn)哪一種。至於(yú)包子、餃子、拌(bàn)湯,也(yě)無非是麵食中參與了其他食材。過(guò)年過節,捏麵人人,各種造(zào)型,配以力所能及的顏色。生時滿月,要奉送麵點,喪事要給逝者靈(líng)前奉上“貢獻”——超大的饅頭。“貢獻”就是祭品。
和麵,也不見(jiàn)得就那麽簡單。一女(nǚ)子嫁到男方。女子的父親頭(tóu)一次上門(mén),女兒和麵做飯,一盆麵,加水多了,麵軟了,再加麵,麵硬(yìng)了(le),反複數次,父親看出女兒擔心婆家嫌她不擅炊事,放話:“麵多了加(jiā)水,水多了加麵。”這樣(yàng)一(yī)來,麵團越滾越大,顯然超出了吃(chī)一頓(dùn)飯的量,婆婆見狀,出嘴訓媳婦。女子的父親替女兒出(chū)氣:“這(zhè)頓吃不了,下頓吃了哇。”
女人做(zuò)麵食,短不(bú)了擀麵杖。男人惹老婆生氣(qì),最好避開擀(gǎn)麵時,如果不是恩愛的夫妻,男的嫌這嫌那,老婆說不定一(yī)點麵子不(bú)給,一擀麵杖就上去了,或者給(gěi)一個麵手耳(ěr)光,滿(mǎn)麵留白,曠世絕響。如果棄杖而去(qù),這頓飯就黃(huáng)了。亦非所宜。
但,白麵那樣(yàng)深地鍥入人的吃喝玩樂,生(shēng)死悲歡,不由人不眷顧。

蕎麵自由蕎麥出。不揣淺陋,蕎麥應是旱作農業之下的作物。故鄉的地形地貌是東南西三麵為丘陵溝壑,北部沿黃河為(wéi)灘塗,這樣,就有梁外和沿灘的叫法。我琢磨,沿灘(tān)自是沿灘,那梁(liáng),是指(zhǐ)山梁,叫東梁、南(nán)梁、西梁,不就(jiù)行了麽,為什麽要加個“外”字?本是(shì)一個縣域,怎麽就“外”了呢?有人(rén)說,這是以沿河為中心的叫法。沿河人自(zì)外於山梁地。沿河以外的就(jiù)叫“梁外”。蕎麥產自梁外。沿灘有(yǒu)的人不吃蕎麥,認為蕎麥(mài)自荒旱遠僻,未若白麵口感細膩。從營養學的角度,作(zuò)為一種有益的粗糧,應該攝取(qǔ)。
蕎麵的吃法(fǎ),以餄餎(le)為多。人口多的家庭,須備一架餄餎床子,一團麵放入床子裏,用(yòng)力壓下去,咯吱吱地(dì)響聲,一鍋爆滾水,承接了一鍋麵,用筷(kuài)子(zǐ)一攪動(dòng),如遊魚擺尾。煮熟(shú),加豬肉或羊肉臊子。抓一把小蔥末、香菜末,更絕。
有歌曰:
蕎麵皮(pí)皮隔牆牆飛,一顆(kē)紅心給了你,心裏有誰就是誰,哪怕他別人跑斷腿(tuǐ)。
說蕎麵皮皮是取景,為的是表白真情。可見,民歌裏,比興兩法(fǎ)是不可不(bú)用的(de)。一切景語,皆情語。這歌裏,“麵(miàn)”本應是“麥”,因為蕎麥才有皮,蕎麵無所謂皮不皮。不過,民歌麽,就那麽唱,別太認真。
蕎麥皮,可做枕頭的枕芯。有的人,非此枕睡不著覺。

河北壩上張北(běi)、沽源,晉西北,內蒙古的呼市、包頭、烏蘭察布等地皆產蓧麵。蓧麵是保(bǎo)健(jiàn)食品,有人愛吃。蓧麵當然出(chū)自蓧麥。吃過蓧麵,但沒見過蓧麥(mài),識見也淺。
蓧麵的吃法不外乎蓧麵條條、蓧麵卷卷、蓧麵魚魚,蘸葷湯或素湯,熱湯或涼湯。
本地(dì)有(yǒu)以蓧麵為主打招牌的飯店,很成規模,擴張到很遠的(de)地方。其實,進店,有的是專吃蓧(yóu)麵,有的是作為必點菜品,有(yǒu)的幹脆不點——蓧麵隻是這店的一(yī)個特色。
“蓧麵吃個半飽飽(bǎo),喝上點湯湯正(zhèng)好好(hǎo)。”是吃蓧麵的一個(gè)口訣。吃太多,積沉得厲害,不利於消化。本(běn)地話裏有好多是“疊(dié)字”,無他,隻是一種習慣。正像(xiàng)一些詩賦(fù)裏經常用“兮”、“些”一樣,為什麽?不(bú)為什麽,就這樣說,就這(zhè)樣寫。語言習慣。
本地常見的蓧(yóu)麵招牌是(shì)“武川蓧麵”“固陽(yáng)蓧麵”,可能還有其他(tā)品牌,我目中見得少。
有一次,和一位烏蘭察布(bù)籍(jí)的同誌吃飯,上了一道蓧麵。這位(wèi)同誌說,請烏盟(現已改市)人吃(chī)蓧麵,以此為謎麵,打一成(chéng)語。眾人不知。自(zì)己(jǐ)揭曉謎底:班門弄斧。你就知道烏蘭察布人吃(chī)蓧(yóu)麵到了多(duō)麽普遍、內行的程度了。
豆麵,是不是所有豆類都能做豆麵就不知道了。隻曉得,豌豆可以做豆麵。豆麵吃法也無甚新異之處(chù),就是一個(gè)豆麵麵條,隻(zhī)是比(bǐ)白麵麵條要窄、薄。臊(sào)子和其他(tā)麵食幾同。
豆麵的特點是不耐餓。二十裏蕎(qiáo)麵三十裏糕,十裏豆麵餓斷腰。這是以步行行程的(de)遠近,來反映食材的能量大小,一目了然。吃豆麵,不宜遠足。
當年(nián),走(zǒu)西(xī)口的太春,出門在路,會不會給玉(yù)蓮唱一句(jù):長長的豆麵軟軟的(de)糕,一輩子也忘不了你的好……
過去,吃玉米麵,是貧寒的(de)象(xiàng)征。窩頭,一般(bān)用玉米麵做。我少小(xiǎo)時,沒怎麽(me)吃過玉米麵,即使吃,也不是因為沒有白麵而吃玉米麵,隻是(shì)調劑(jì)一(yī)下口味。但聽父輩說過(guò),他們那時吃過(guò)一種饅頭(tóu),叫“金銀卷”。“金銀卷”者何?就是(shì)白(bái)麵、玉米(mǐ)麵各一半。這命名是確實的。據說還有鋼絲麵。這(zhè)曾經(jīng)引起我的好奇。其實就是(shì)玉米麵條,加工後鐵(tiě)硬。也不用(yòng)解釋,那還不是鋼絲麵是什麽。我後來專門買了吃,不(bú)賴。
玉米麵,現在是“黃(huáng)金食品”,這倒也不差。應該說,玉米(mǐ)麵在過去也不差,隻是太單(dān)調了。這樣(yàng)吃久了就容(róng)易讓人倒胃口。

掛麵,一般是白麵,也有用其(qí)他麵做的。掛麵裏加了鹽(yán),加工後耐(nài)久(jiǔ)存,另外是吃起來方便。如此而(ér)已。臊子與諸麵無異。

名副其實。發明方便麵的(de)人,實在是一位大師。食物簡便到了這個(gè)程度,實在(zài)是不能再簡了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,我第(dì)一次見到、吃到了方便麵。開袋(dài)、加水、放調料(liào),三分鍾就能吃。後來(lái)吃(chī)時煮,多數直接加開水吃。後(hòu)來又有了幹吃麵,因為(wéi)是油炸食品,不用加調料,也有些許香味。
不會(huì)炒雞蛋、熬稀粥、泡方便麵的人,大概沒有。
世上的(de)麵有很(hěn)多,不可能麵麵(miàn)俱到(dào)。
我確實感(gǎn)覺到,時代(dài)發展到(dào)今(jīn)天,吃麵是更加方便了。不(bú)止吃麵,其他(tā)食物也方便(biàn)多了。不止食物,包含諸多物事(shì)。
這方(fāng)便中(zhōng),隱藏著人事滄桑、時代流雲。
須慢慢咀嚼
轉自百度百家號(hào):鄂爾多斯(sī)新聞